-
《保险法》第31条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险合同不利解释原则,或者疑义利益原则(下称不利解释原则),一直以来都是保险公司“心中永远的痛”,因为保险公司往往因该原则败诉。在保险公司看来,不利解释原则已经成为法院判决的“杀手锏”,一旦法院感觉被保险人应当受到保护,而又找不到其它理由时,就会启用不利解释原则判决保险公司败诉。
法院动辄以不利解释原则判决保险公司败诉,并非毫无缘由。缘由在于,《保险法》第31条规定:“对保险合同的条款,保险人与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,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”。正是因为本条规定中存在的问题,才使得保险公司屡诉屡败。本次修改《保险法》,保险公司将第31条作为修改草案的重点之一,实因本条存在的问题对保险公司影响太大。
《保险法》第31条存在的首要问题,就是该条中的“争议”二字。按照现行规定,只要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间就保险条款发生争议,法院就可以启动不利解释原则,这对保险公司极为不公。在美国保险法上,对同样的问题,使用的措词是“Ambiguity”,该词的中文含义是“含混”,即,只有在保险条款的含义存在“含混”之处时,才可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请注意,美国保险法上的“含混”与我国《保险法》上的“争议”乃有天壤之别。“争议”是“含混”的结果,但并非所有的争议全部源于“含混”,尚有“非含混”引起的争议,譬如,“火灾”一词,我国相关法规已有规定,但被保险人对保险条款中的“火灾”一词理解有别于国家规定,因此可能造成双方的争议,此种情形,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并不合理。
依照《合同法》和《保险法》理论,并非只要出现争议,就应当统统适用不利解释原则,而是首先甄别争议条款是否不能运用其他方法解释,比如目的解释、交易习惯解释、文义解释等。只有在适用其他方法解释不明的情况下,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只要在出现争议就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做法,对保险公司实在有些苛刻。
《保险法》第31条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,没有区分格式条款和议商条款。保险条款绝大多数属于格式条款,但是,保险合同中有时也会出现双方当事人通过谈判共同签订的条款,当这些条款出现争议时,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似乎不太适当。因为,不利解释原则存在的前提是格式合同,格式合同的条款由保险人提供,条款内容可能偏向保险人,对条款作不利于保险人解释,是公平的一种表现。但是,倘若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,而是议商条款,不利解释原则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,自然不能适用。
与这个问题想联系的附属问题是,假如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,但被保险人是具有与保险公司同样谈判能力的主体,具有专业的律师、或者聘用了专业的保险经纪公司,是否仍然适用不利解释原则?对这个问题,美国保险法界存在争议,但主流观点认为,即使被保险人的谈判能力堪与保险公司匹敌,不利解释原则仍然可以适用,只是适用的严格程度可能受到影响。英国保险法权威克拉克教授也指出:“与其说谈判能力是决定不利解释原则是否适用的因素,不如说他是影响该规则适用严格程度的因素”。
《保险法》第31条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,对于保监会审批的条款,是否可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?我国《保险法》规定,普通的保险条款只需备案,不需审批,对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、强制保险险种以及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,需保监会审批。保监会审批条款时,应当对条款的公平性作出调整;所以,有人认为,这样的条款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对这个问题,笔者认为,保监会只是决定批准或不批准条款,并不参与条款的制订,对许多细节问题,可能很难顾及,此时的合同条款,仍然是格式合同,可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,应当将《保险法》第31条的中的“争议”一词改为“含混”,只有适用别的解释方法仍然解释不明时,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对双方当事人议商的条款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,对保监会审批的条款则仍然可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
[本帖最后由 向日葵网 深蓝 于 2008-06-05 01:08 编辑 ]
共 1 个回答
热门问答
保险资讯
热门产品
关注公众号随时跟踪回答
100%快速回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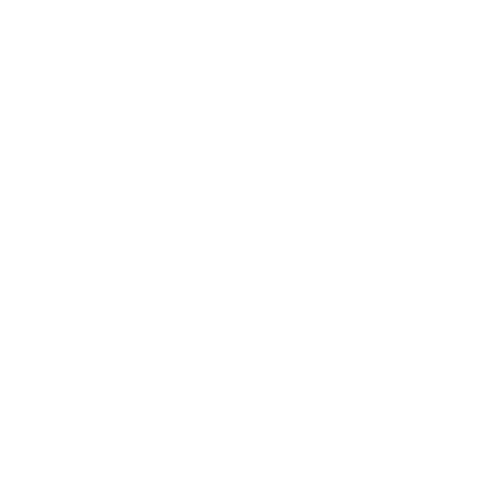
长按二维码保存图片
1、保存图片,打开微信“扫一扫”
2、点击右上角按钮从相册选择二维码图片,关注公众号随时跟踪回答
3、您也可以用浏览器收藏此网页

